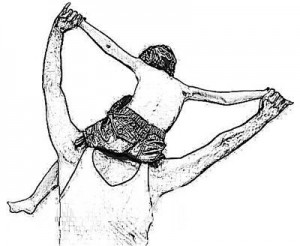前言: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期待他牵我的小手,用胡渣蹭我,对我说你这个坏蛋,长大了想要做什么?
by 灵致
当我开始写这篇关于他的文章时,我在西雅图,他在天门。
仿佛我们的距离,不是隔了一个太平洋,而是隔了一条浅浅的河,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我在此岸,他在彼岸。他向我招手,说出那句他最爱的经典台词:XX,你吃饭没有?
我透过酒店的窗,望了望远方的雪山,是一种圣洁和遥远的感觉,就像此刻我对他的回忆。
这些年,我写过很多东西,但关于他的东西很少。我给很多人讲过笑话,把他们逗得哈哈笑,但是我不曾给他讲过任何笑话。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偶尔电话里面他爽朗的笑声。呵呵,呵呵呵呵的节奏。
都说今天是父亲节,我也不能不知道。最近这个星期,每天早上开车去公司,电台的主持人总是不断的提醒人们:Hello, Everyone! Fathers’ day is coming. Give a call to let him know how deeply you love him (同志们!父亲节到了!给他一个电话,让他知道你爱他很深!)
就在昨天,诗琳问我:打不?
我问:你打不?
她沉默,说:“他貌似不Care,也根本不知道。”
“嗯,是的,他也不care 。”我叹了口气,我知道男人很难做到感情细腻,所以大部分孩子和母亲的关系要亲密一些。
事实上,他也和我亲密过。只是,我们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很不相同。
我试图在脑海里面搜索关于他的点点滴滴的记忆,想要找到我在生命的最初对他的第一个印象,结果找到的是那个我很久未曾记起的片段:
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月亮很亮,时间已近天明。
我正睡意朦胧,突然听到有人在窗外轻声呼唤母亲的名字。 我睁开眼看看窗外,月光照亮着窗外的枣树,好早好早。
然后不一会儿,我就感觉有人进了房间,睁开眼见是他。
他就笑眯眯的,过来抱着我,用他满是胡渣的脸一阵猛蹭,然后边说“啊!我的儿醒了,我的儿醒了哇!”
我刚醒,哪经得住他那一番磨啊,立马哇哇叫,“好痛啊,好痛啊”, 他就放开我,一下下用他厚重的巴掌隔着被子拍我的背,“这个小东西,还知道痛哇!”。
我就不理他,头扎进被子里面不愿意出去。
不一会儿,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立马出去一会儿,然后进来说,“XX,来看,我给你的!”
我闻声从被窝里钻出来,看了看,是很漂亮的饼干。没有包装袋,但是我拿了一块,很好吃。我就笑了笑,屁颠屁颠吃起来。他笑笑,放到一个塑料袋里,然后说:都是你的,带去学校吃!
那天成了我在学校里非常开心的一天,很多其他朋友都围着我,要我给饼干吃。我就分了一点,然后偷偷的将剩下的藏好。想着他明天会不会还带些回来。
那些天,他每天都是下午出去,然后凌晨回来。我问母亲他去干什么了。她说,他啊,去赶板车了。于是我低头不说话。
想起来,赶板车是件很辛苦的活。基本就是用一辆板车,自己充当牛的角色,拉着很重的货物给人送到指定地点。我想他肯定很累,因为每次回来都是满头是汗,满脸写着疲惫。但他总会给我们带点小吃的,我们都很喜欢。
我并不记得那种生活他持续了多久。多年以后,当他在城里做生意的时候,有几次我看到有人帮他拖完板车之后,他会多给一点钱,然后很客气的感谢别人。然后他会看着我,笑着搓搓手说:你知道的,他们很辛苦,往往需要的是一点点尊重,呵呵呵呵。他笑的时候很憨厚,时至今日亦不改本色。
他在我记忆里,是一个老牛般的角色。这也是他一直欣赏的角色。我表示认同,是因为我所看到的老牛,都非常强壮,满是肌肉的感觉。 他就是这样的体格,非常壮实,虎背熊腰个不高。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他曾经年少的时候被选上飞行员,但要去西安参加复检而家里又拿不出路费,于是只好痛苦的作罢。
小时候,我眼里的他总是力大无穷。我打不开的罐头,只要找到他,就直接用手一拧,大半机会那盖就开了。
冬天的时候,他会去挖藕。那是他的强项。深深的藕塘里,他就一铲一铲的往外掀泥巴,三下两下就可以拿出一根人这么长的藕。一天之中,他可以挖好多好多,洗好了拖去换钱。
有时候我去看他,他就隔得老远老远就笑呵呵的喊我过去,然后挑些藕的拱头(最前面的那节最嫩的藕),在水里洗洗,然后给我。我就嚼吧嚼吧放在嘴里吃。他喜欢问我“好吃吗?”当我回答好吃的时候,他就笑。
他其实很爱孩子,爱到深处,让母亲都觉得他似乎忘了自己是谁,也忘了母亲是谁。
小时候家里穷,全指望着几亩地过生活。加上我们要上学,需要开销,这些并不是件轻松就可以搞定的事。还好他很聪明,读过书,有点知识,而且非常吃得起苦。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清苦而充实。
那时候我们小孩经常要帮着家里干活。家里秋天会收很多棉花,小孩要帮着拆棉花。 家里有种过棉花的同学们都知道棉花摘回家之后要用手将棉花的棉絮部分从壳里拆出来,才能够拿去卖。
正是因为这样,在棉花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剥棉花。大人和小孩,齐聚一堂,就那么剥啊剥啊剥。
父亲做事虽然给力,但是剥棉花这种绣花功夫他不上道,经常剥着剥着就睡着了,头就那么一晃一晃的。我们也不打搅他,让他那么晃。他经常晃久了就醒了,然后茫然的看看我们,噜吧噜吧嘴,接着剥,然后接着打瞌睡。
为了刺激小孩的积极性,大人的做法就是剥一斤棉花算多少钱,比如一两毛,但是我们小孩子剥得很起劲,心里想着买雪糕的钱就指着这个啦。
我当时拼命剥,甚至晚上不愿意去睡觉,就是为了多弄点公分。他心疼我们的时候,经常说:你们两个去睡觉吧,我给你们算多少斤,不用剥了。
我一个秋天下来,攒了两块一毛钱。我经常看着账本上的那个数字,很是高兴我要拿这笔巨款去干什么。
有那么一个晚上,他在洗澡,对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的钱借给我,我要去买东西,但是缺钱。 我噜吧噜吧嘴,挺不乐意。他就笑,呵呵呵呵,一定还和一定还。
我自然不好说什么,反正一直在账本上,也没有看到过票子,就那么滴。不过貌似我们两个后来都将这事给忘了,至今这两块一毛钱都没有兑过现。这也看得出他当时手头紧。
也不记得过了几年,家里终究太拮据。父亲似乎被逼上了梁山,即使之前他干过生产队长,开过豆腐铺,种过蘑菇,想过很多办法,但终究抵不过增产不增收的惨痛规律。
母亲的几个弟弟陆续在城里做起了生意,混得不错。她就开始怂恿父亲进城。
父亲老实,不愿意。他觉得他就适合在村里做点啥。母亲不同意,知道他怕输。她就一怒之下去借了两千块钱,塞给他,说:你去!赔了就赔了,家里的事不要你管,我来挑!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如何回答的,估计他也就噜吧噜吧嘴,看看母亲彪悍的眼神,也就默许了这件事。大部分时候,母亲怕他,但是母亲发威的时候,他也知道不对着干是个明智的选择。
刚开始的时候,日子很艰难。他回来每次都是闷声喝酒,喝醉了酒空口说胡话。有天我抱着他的腿,他摸摸我的头,说:其实我希望走在街上被车撞死算了。说完他接着喝,我不懂他为什么说胡话,母亲不好受,就走开。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日子,他本钱不多,做水产品生意本金不多很难做大,别人也不care这种小散户,自然言语多有怠慢,也不耐烦。 而他恰恰是个自尊心很敏感的人,觉得是种侮辱。他也只能借酒消愁。
即使不开心,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他天中饭就是一个馒头,他不肯买任何东西。 母亲看不下去,就让我送饭。我就常常步行一个小时去给他送饭,他对此很高兴,觉得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也不记得我坚持了多久,总是那是很遥远的一段路。
我小学毕业后,他非常想我去城里上学。 因为他读过书,但是只到初中毕业就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而被迫离开了学校。尽管他很渴望继续,可是生活所迫非自己所能控制。
他们这一代的人最典型的特色就是喜欢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委托给下一代。于是,他就把理想都给了我。
我去了城里,一切陌生而又新鲜,城里的孩子玩的和我小时候很不一样。我就开始试图融入他们的环境。
可是父亲节俭,中午做饭有时候相当凑活,在花费方面过于节俭,导致我手头很是紧张。平时没有钱打游戏机和与女孩子们出去玩。
我自然有我的过法,和很多相好的朋友迅速打成一片。就这样猝不及防间,我也进入了叛逆期。
我知道他的节俭是因为生意局面打不开,终究是小打小闹,苛捐杂税贵,我上学也不是小费用。
可是我不理解,我只知道班上同学去滑冰,各种玩耍,过各种生日,而且我也迷恋打游戏机。 我也有参与的渴望,尽管我某些时候理解他。
我总有办法能够从他那里弄到钱,然后一个人去挥霍。渐渐的,我开始和他顶嘴,和他对着干。他一般都忍着。
直到有天我当着他很多同行的面说了很多刺痛他的话,让他很尴尬。那天晚上,我被他揍了一顿。我估计记仇了一阵子,也就被他的关心打动了,不了了之。但偶尔看到他很辛苦,我也心疼他。
那年,我做过一些荒唐事。包括有次和别人赌狠,从一个比一层楼还高的地方跳了下去,而下面是水泥地。尽管我尽量用我知道的技巧,比如用腿缓冲缓冲,但是终究是双脚着地后差点废了 — 一双脚踝肿得老高老青,无法行走。
他并没有问过我是神马情况搞得我如此惨烈,就去买了一瓶烈酒,用火点燃,然后趁着热给我做按摩。在他的关怀下,我算是一个星期后可以走路了。
他以为我非常乖,其实我一点也不乖。我偷偷去打游戏机,偷偷陪女孩子过生日,在学校打架,帮助同学抄作业,考试作弊等等。可是我每次都是班上第一名,因为那是一个全校最差的班。
他很高兴,不管我在做什么,总是以我为骄傲。
不久以后,我到了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我开始觉醒,我开始痛心他的辛苦生活。觉得那不应该是他永远该过得生活。
我成绩渐渐在全校拔尖,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全面都很在行。我开始写日记,记录我和他的生活,记录我们睡一起的日子,记录他为我做的一切的一切。
他依旧以我为傲,干活拼命努力。他从来没有其他娱乐活动,睡觉少,醒了就干活。从来都是5点钟就醒了,晚上十点左右睡觉。 白天不停歇,没有周六周末。一年365天之休息大年初一那天,然后其余的时间都在干活。
在他的坚持不懈下,生意渐渐越做越好,在同行中算做的很不错的。
于是他常常向我讲他的生意经,我也装作眼神发亮的听他讲那些他曾经给我讲过不下于百遍的话。
我和他生活六年后,我上了大学,离开了他,每年很少回来,即使回来也时间极短。我没有注意到,每次我离开家,他都非常不舍得。但他还是会和我说:你要以事业为重,有多高,飞多高。不要恋家。
我似乎天生就适应能力很强,在哪里都能一个人过得很好,不像别人那么恋家。所以家里电话也少打,打也是打给母亲,因为他话少,不八卦,只是不管时间几点,总是问我吃了没有然后嘱咐我注意身体。有些要求他甚至还要妈妈来转达给我。
多少年后,我回家乡,去看他住的地方,他还挂着我初一的学生证。那上面的少年,一头短发,坚定的眼神,没有笑容,在白衬衫下显得很倔强。 他说:你这张照片很帅哇!
我只听过他说过他这个儿子帅,没有说过任何其他人。 我笑笑,笑纳了这种说法。
可是他也有抱怨,说我给他打电话少,但不是和我说的,而是和他的同僚,然后同僚偷偷告诉我的。我笑笑,在心里想要给他多打点才行。
他看报,很关心国家大事。但他不喜欢我激烈的政治观点,和近乎强势的反毛情节。他怕我在政治上犯错误,而我,一直是他眼里的那个不惜激烈辩论于集市的愤青。
他说希望我入党,尽管我鄙视党。但是还是入了,入党的时候我没有去宣誓,但我在拿到党员证的时候告诉了他,说你儿子我入党了。他说好,那就好,那就好。他不知道之后我的党员证也不知道弄到了何方去了。也不知道我出过的时候没有申请保留党籍。
我出国的时候,他老骄傲了,觉得自己的儿子了不起。 他和我说,你要是需要钱,我帮你搞。
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用不着。 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妈。
他点点头。
我在美国的时候,每次打电话,他总是不忘嘱咐我要保重身体,不要心疼钱。 其实他不知道,我已经深深受他的影响,很节省,尽管近些年在这方面有些放松,但我依旧能够感受他对我的影响。
我一直佩服他的精神 — 他从来不玩,做事很投入,很坚持。
我一直说我赶不上他的三分之一伟大,因为我没有那么专心和坚持,也没有他那么吃的起苦,也不可能像他那样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牺牲的精神。
我很骄傲我来这个世界之后有他的陪伴,和他的精神鼓舞。
想起他的时候,我总会记起那么一幕: 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晚上必须回家,我就在南湖一个路口目送他骑着自行车离开,直到消失在转弯处。
那个背影,一直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虽然无言,但是大爱。
在这个属于他,以及千千万万的如你一样伟大的男人的日子,我想对他说声节日快乐。
父亲的感情,深似大海,铭记我心,从未褪色,千山万水,不减此情。
灵致
2012年6月17日
西雅图